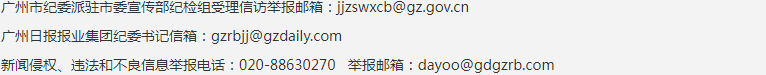(作者:郑逸斌)清季同治光绪年间,丁日昌的名字始终与洋务运动的浪潮紧密相连。作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先驱者之一,他以福建巡抚之职督办船政,擘画海防,为晚清飘摇的江山社稷奔走呼号,试图以一己之力挽狂澜于既倒。然而,宦海浮沉,世事磋磨,这位洋务干将终究难逃病体的拖累与朝堂的非议。晚年的丁日昌辞官归里,(史载丁日昌于1877年8月因病离职回籍休养。)蛰居于广东揭阳,在病榻之上,他写下一封致船务大臣黎召棠的信札。这纸尺素,饱含沉郁,道尽了一位老臣心系社稷却又病魔缠身、屡遭误解的委屈与无奈,也为后人窥见晚清士人在时代夹缝中的挣扎与坚守,打开了一扇窗。

丁日昌写这封信时,已是58岁之后的暮年。彼时的他,卸去了一身的官场繁冗,却并未换来身心的安宁。远离了京城的喧嚣与船政的繁忙,揭阳的庭院里,只剩下病骨支离的他。信的开篇,便满是人情的温度与遗憾:“顷奉复函,敬悉一切。嫂夫人仙逝,兄以道远竟不克亲奠灵帏,殊深歉仄。”寥寥数语,既是对友人丧亲之痛的慰藉,也暗含着自身病弱无法远行的无奈。这份遗憾,是暮年之人对人情世故的珍视,也为整封信奠定了沉郁感伤的基调。
紧接着,信中谈及黎召棠春初赴闽之事,丁日昌的笔触陡然多了几分细致与热忱。他主动为友人规划行程,提及此前福建船局吴维允“济安船极熟,由粤到闽水路并熟,由汕头到揭阳水路来过敝处三次”,建议黎召棠预先知会济安船,乘此船携家眷从粤出发,经香港、汕头、揭阳、厦门,最终抵达马尾。他甚至贴心地补充,“是船可装家眷,似瀛眷亦可附乘此船也”。这番絮絮叨叨的叮嘱,绝非寻常的客套。于丁日昌而言,船政是他半生心血所系,济安船更是他熟悉的“老伙计”,提及船政相关的人与事,他便不自觉地流露出当年督办船政时的干练与热忱。这份热忱,是刻入骨髓的职业本能,更是他对船政事业难以割舍的执念。
然而,这份对船政的热忱,终究抵不过病体的拖累与朝堂的误解。信中最动人也最令人扼腕的部分,便是丁日昌对自己“引病不出”的剖白。黎召棠曾劝他出山,这份美意,他感念至深,却只能无奈回绝:“弟委实病不能行,并非能行而不欲出。”为了佐证此言非虚,他特意提及李鸿章的来信——“都中有良材者,两宫颇怪,弟引病偃蹇不出等情,即都人士亦多疑弟是假病者”。寥寥数语,道尽了他的委屈与心酸。
丁日昌作为晚清洋务运动的实干家,从办理江南制造总局到督办福建船政,从整顿海防到倡设电报,他的一生,都在为富国强兵的理想奔波。壮年之时,他未尝不是意气风发,渴望以一腔热血报效国家。即便是暮年病卧,他也坦言“兄此时一出,必可稍展平生所学,岂有不愿出之理”。这份报国之心,炽热而赤诚,从未因岁月流逝与病痛折磨而有半分消减。可叹的是,朝堂之上,流言蜚语如影随形。两宫的责问,士人的猜疑,像一张张无形的网,将他紧紧缠绕。他只能苦笑着邀请黎召棠“公明春到敝寓,亲见即可知兄之真病矣”。这一句恳切的邀约,背后是不被理解的孤独,是英雄迟暮的苍凉。
更令人心酸的是,丁日昌对自己的仕途早已心如明镜。他坦言,“比地高燥,足疾从此或能少愈也未可定”,病愈之后,若蒙恩赏以闲散京秩,尚可勉力趋公,若是外官,则“自揣精神衰惫,断不能胜任矣”。这番话,不是推诿,而是对自身状况的清醒认知。晚年的他,早已不复当年的精力充沛,缠绵病榻的苦楚,只有自己知晓。他所求的,不过是一个能稍尽绵薄之力又不至过劳的闲职,这份卑微的期许,却在“假病避事”的流言中变得遥不可及。
在信中,丁日昌还袒露了自己进退维谷的深层原因:“兄五月间疏辞海防六不胜任中有不知兵一条,其言极为结实,此何不能作督之明徵。总之,兄未尝不欲以一死报国,无如都中物议纷纭,一事尚未办成而谤书业已盈箧。”这才是他“足将进而趑趄,口将言而嗫嚅”的根源。晚清的朝堂,早已不是实干家的舞台。派系倾轧,流言四起,一件事尚未开始推行,弹劾的奏章便已堆满了书箧。丁日昌深谙此道,他怕的不是辛劳,而是一腔热血付诸东流,反落得满身污名。他不是看破了富贵功名,而是看透了朝堂的荒诞与凉薄。这份看透,不是消极避世,而是历经沧桑后的无奈与悲凉。
当谈及朝廷命黎召棠整顿船政、不欲仍造旧船时,丁日昌的笔触又多了几分期许。他说“公到任后想必有一番规模也”,简单一句话,饱含着对船政事业的殷切期盼,也暗含着对后继者的信任与鼓励。他虽已远离朝堂,却始终盼着船政能走出新的道路,盼着大清的海防能日益坚固。这份拳拳之心,感人至深。信的末尾,他写下“公见过时当畅谈三日三夜耳”,这是老友重逢的热切期盼,也是压抑许久的心事,渴望一吐为快的迫切。而那句附言“闻惟允有辞差之意,公留之否”,则又将思绪拉回船政人事,尽显他对船政事务的牵挂。
纵观这封信札,没有华丽的辞藻,没有激昂的论调,却字字句句皆是肺腑之言。这是丁日昌晚年心境的真实写照,也是晚清一代士人命运的缩影。他们怀揣着富国强兵的理想,在时代的浪潮中奋力前行,却终究难逃病体的拖累与朝堂的倾轧。心怀赤诚却身不由己,志在报国却病榻难赴,这份委屈与无奈,在历史的长河中,化作一声悠长的叹息。
除却文字间的沉郁心境,这通信札的书法亦颇具品鉴价值。丁日昌的书风根植于颜体,深得颜真卿楷书宽博雄浑、骨力洞达的精髓,却又不为碑帖所缚,尽显尺牍书写的自然意趣。信中笔画丰腴沉稳,起笔收锋间无刻意雕琢之痕,转折处圆劲浑厚,兼具筋骨与气度;章法排布随文势流转,字距行距疏密得当,虽为病中执笔,却笔意连贯,不见滞涩,将一位洋务重臣的刚直性情与暮年心绪,皆融于笔墨起落之间。这份自然天成的书写状态,让信札超越了单纯的文献载体,成为兼具史料价值与艺术审美价值的翰墨遗存。
这通信札更具非同寻常的文物价值与艺术价值的是,此信原为民国南社名士李沧萍旧藏。李沧萍(1897—1949),原名绍基,字菊生,广东丰顺县小胜乡羊公坑人。早年就读于广东高等师范学校、北京大学中文系,1924年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留学。归国后历任教育部秘书、北京大学讲师,长期担任国立中山大学教授。李沧萍得此信札后,精心装池,又邀晚清翰林,番禺张学华,以及岭南文史学家汪兆镛题跋。张学华出身科甲,曾任金山书院主讲,与潮汕因缘不浅;汪兆镛博通文史,尤擅金石考据。他们在题跋中讲述了其父辈与丁日昌的交善,不仅对丁日昌其人其藏书的品评,更以自身的声望与学识,为这件信札提供了权威鉴定。一纸信札,集名人手迹、名家递藏、学人题跋于一身,既承载着晚清洋务重臣的心境剖白,又兼具文献价值与收藏价值。
丁日昌一生对洋务的实践,为近代中国的发展埋下了火种;而他晚年的这封信札,则为后人留下了一个鲜活的、有血有肉的士人形象。纸短情长,尺素之上,是一位老臣的耿耿孤忠,是一段历史的沉沉回响。当我们拂去岁月的尘埃,重读这封信,依然能感受到那份穿越时空的委屈与无奈,也更能读懂晚清士人在时代变局中的坚守与悲凉。